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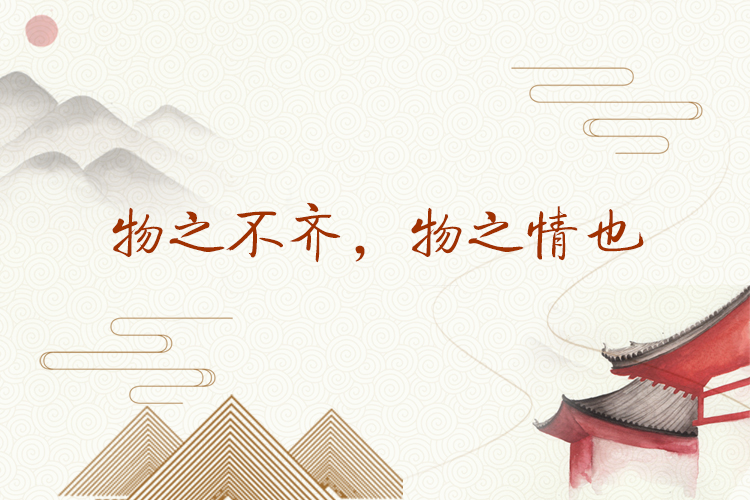
“物之不齊,物之情也”是2015年3月28日,習(xi) 近平總書(shu) 記在博鼇亞(ya) 洲論壇年會(hui) 開幕式上發表的主旨演講中引用的。他說:“中國古代思想家孟子說過:‘夫物之不齊,物之情也。’不同文明沒有優(you) 劣之分,隻有特色之別。要促進不同文明不同發展模式交流對話,在競爭(zheng) 比較中取長補短,在交流互鑒中共同發展,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(wei) 增進各國人民友誼的橋梁、推動人類社會(hui) 進步的動力、維護世界和平的紐帶。”
“物之不齊,物之情也”的出處,是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。

中華書(shu) 局出版《孟子》
《滕文公上》是《孟子》中的一篇。這一篇共包含五個(ge) 相對獨立的部分,分別討論了五個(ge) 不同的問題,所以一般將其分為(wei) 五章。“物之不齊,物之情也”出自《滕文公上》的第四章。這一章的主要內(nei) 容,是孟子對以許行為(wei) 代表的農(nong) 家學派的批評。
農(nong) 家學派,也是諸子百家之一,這一派最推崇的人是神農(nong) 氏,他們(men) 的主張,用最簡短的話來說,就是要重視農(nong) 業(ye) ,最好無論君臣,人人都親(qin) 身從(cong) 事農(nong) 業(ye) 勞動,自力更生,自給自足,將商品交換減少到最低程度。對於(yu) 以許行為(wei) 代表的農(nong) 家學派,我們(men) 要說的是,重視農(nong) 業(ye) 生產(chan) 是對的,但把農(nong) 業(ye) 淩駕到一切行業(ye) 之上,特別是要人人從(cong) 事農(nong) 業(ye) 勞動,這看法就太偏頗了。因為(wei) 人類的發展,離不開分工協作,這才是社會(hui) 能夠不斷進步的根本原因。
當時農(nong) 家的代表人物許行到滕國,受到了不少人的熱烈追捧,其中有一個(ge) 叫陳相的人。陳相原來是儒家的信徒,後來改投許行門下,他見到孟子,向孟子宣揚許行的思想。孟子於(yu) 是在陳相麵前,批駁了農(nong) 家的種種謬誤之處,其中之一,就是農(nong) 家所主張的簡單的定價(jia) 原則:別管是綢是布,隻要尺寸相同,價(jia) 格就都一樣;別管是絲(si) 是麻,隻要重量相同,價(jia) 格就都一樣;別管好鞋壞鞋,隻要尺碼一樣,價(jia) 格就都一樣。這樣的話,就是小孩子上街買(mai) 東(dong) 西也不會(hui) 受騙,國家就沒有爾虞我詐這些亂(luan) 七八糟的現象了。正是在對這一主張的批駁中,孟子說出了本講提到的名言:“夫物之不齊,物之情也。或相倍蓰,或相什百,或相千萬(wan) 。子比而同之,是亂(luan) 天下也。巨屨小屨同賈,人豈為(wei) 之哉?從(cong) 許子之道,相率而為(wei) 偽(wei) 者也,惡能治國家?”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:物品千差萬(wan) 別,這是由各自不同的屬性決(jue) 定的。不同的物品,有的價(jia) 格差一倍,有的價(jia) 格差五倍,有的甚至相差十倍百倍,千倍萬(wan) 倍。如果把它們(men) 放在一起用一個(ge) 標準看待,就是擾亂(luan) 天下。打個(ge) 比方,工藝粗糙的鞋和工藝精良的鞋,隻要尺碼一樣,就一個(ge) 價(jia) 錢,那麽(me) ,誰還肯做工藝精良的鞋子呢?
我們(men) 將這句話放在整個(ge) 文章的語境下,就可以看出,“物之不齊,物之情也”包含著不可偏廢的兩(liang) 層意思:
首先,事物是千差萬(wan) 別的,這是由它們(men) 不同的本性決(jue) 定的;其次,也是更加重要的,因為(wei) 千差萬(wan) 別,就不能用大小、輕重、長短這樣外在、單一的標準簡單地去衡量。一件事物,可能有千萬(wan) 倍超越類似大小、輕重、長短這樣簡單的衡量標準之上的價(jia) 值。
然而,對孟子“物之不齊,物之情也”的理解,也常常會(hui) 有兩(liang) 種偏頗。
第一種偏頗,是過於(yu) 強調“物之不齊”,而忽視了“物之情也”。特別是這句話後麵緊跟著“或相倍蓰,或相什百,或相千萬(wan) ”。這就很容易造成一種誤解,似乎孟子是刻意強調事物之間的價(jia) 值差距。
第二種偏頗,是過於(yu) 強調“物之情也”,而忽視孟子在前麵清楚說出的“物之不齊”,以及後麵說到的“或相倍蓰,或相什百,或相千萬(wan) ”。仿佛孟子是在用事物的個(ge) 性特征取消對事物進行價(jia) 值判斷的共性標準。
實際上,這都不是孟子的本意。找到孟子的本意,需要在上下文中去仔細揣摩。在本章中,陳相拋出了許行的兩(liang) 個(ge) 判斷標準:第一,用能不能堅持農(nong) 業(ye) 勞動來判斷一個(ge) 君王是否賢能;第二,用尺碼、重量這樣簡單的度量衡來判斷物品的價(jia) 值。正是在駁斥許行那簡單的價(jia) 值判斷標準時,孟子才說出了“物之不齊,物之情也”的話語,所以這句話所強調的重點,是不能以簡單的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價(jia) 值,而絕非事物之間沒有差別,或者事物的價(jia) 值本來就差別很大。
為(wei) 什麽(me) 我們(men) 在這裏如此詳細地辨析孟子的本意?因為(wei) 隻有清楚孟子的本意,才能正確地看待其他文化類型的國家和地區、民族,才能更好地理解當今不同發展模式、不同文化類型的國家與(yu) 地區、民族之間既有競爭(zheng) 、又有合作的交流方式,真正做到在競爭(zheng) 比較中取長補短,在交流互鑒中共同發展。
在過去的很長時間裏,因為(wei) 西方科技長期居於(yu) 領先地位,所以一些西方人氏就滋生了很強的文化優(you) 越感,自覺或不自覺地用西方的標準簡單地衡量其他國家或民族的文化,並以衡量的結果來判斷其他國家文化的高下優(you) 劣。這種態度由來已久,並且一度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產(chan) 生了很大影響,甚至那些國家與(yu) 地區的部分人也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這些標準,並以此衡量自身文化,進而產(chan) 生了很強的文化自卑和文化虛無主義(yi) 。
然而,科技並不是文化的全部。文化的內(nei) 涵是極其豐(feng) 富的,舉(ju) 凡人類在征服、改造自然,以及在塑造、提升自我的過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精神和物質財富,都包含在文化的範圍之內(nei) 。文化從(cong) 外至內(nei) 包含著四個(ge) 層麵:器物層、製度層、風俗層、心理層。在器物的層麵上,確實是有高下優(you) 劣之分的,堅船利炮就是要優(you) 於(yu) 大刀長矛,飛機導彈就是要優(you) 於(yu) 火槍弓箭。但器物層隻是文化層麵中最表麵的一層,而且它也是變動最快的。除了器物層,文化的其他幾個(ge) 層麵也就是製度層、風俗層、心理層所包含的那些內(nei) 容都是很難、或者完全無法以某個(ge) 標準得出孰優(you) 孰劣的結論的,比如你就無法比較《紅樓夢》與(yu) 《悲慘世界》的好壞:它們(men) 隻有特色之別,而無高下之分。
所以,用判斷科學技術的標準去衡量一個(ge) 國家或民族的文化,並得出“優(you) 秀”或“低劣”,“先進”或“落後”的結論的,都是極其荒謬的,這和許行用尺寸大小來決(jue) 定商品的價(jia) 格,用是否堅持農(nong) 業(ye) 勞動來斷定一個(ge) 人是否賢能一樣,是極其荒謬的。如果用這把簡單的尺子,來衡量其他國家或民族,並以之作為(wei) 彼此交往的依據,造成的隻能是彼此的隔閡與(yu) 傷(shang) 害。
但是,我們(men) 不能簡單地用衡量科學技術的標準來衡量文化,也並不是說不同文化之間就不能比較。實際上,不同民族、不同國家之間的差別是客觀存在的。但差異不意味著絕對的優(you) 劣,所謂“長者不為(wei) 有餘(yu) ,短者不為(wei) 不足。是故鳧脛雖短,續之則憂;鶴脛雖長,斷之則悲”(《莊子·駢拇》)。這種差異,不僅(jin) 構成了文化多樣性,使我們(men) 這個(ge) 世界變得豐(feng) 富多彩,更構成了各自不同的比較優(you) 勢;正是這種豐(feng) 富多彩與(yu) 各自不同的比較優(you) 勢,才決(jue) 定了各個(ge) 國家民族之間交流合作的可能性與(yu) 必要性。在文化交流中,對其他的文化,我們(men) 要抱有一種同情之理解,充分理解和尊重這種差異性,這樣我們(men) 在交流中才會(hui) 更加寬容;對待自己的文化,要充分了解自身的長處與(yu) 短處,既利用自己的比較優(you) 勢揚長避短,又正視自己的不足取長補短。
習(xi) 近平總書(shu) 記在《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的講話》中說:“一體(ti) 化的世界就在那兒(er) ,誰拒絕這個(ge) 世界,這個(ge) 世界也會(hui) 拒絕他。萬(wan) 物並育而不害,道並行而不相悖。”在全球化勢不可擋的今天,跨文化的合作交流是一種必然,而隻有理解和接受“物之不齊,物之情也”的觀念,才能以更開放寬容的心態參與(yu) 到彼此的交流合作之中。交流合作得越多,彼此的了解也就越多,作為(wei) 個(ge) 體(ti) 的我們(men) 也就越能享受到更為(wei) 豐(feng) 富的物質與(yu) 精神成果,而作為(wei) 同一個(ge) 物種的人類也就越緊密地聯係在一起,成為(wei) 一個(ge) 充滿友愛精神的命運共同體(ti) 。
關(guan) 於(yu) 我們(men) 聯係我們(men) 網站地圖 用戶調查
ky体育中心 版權所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