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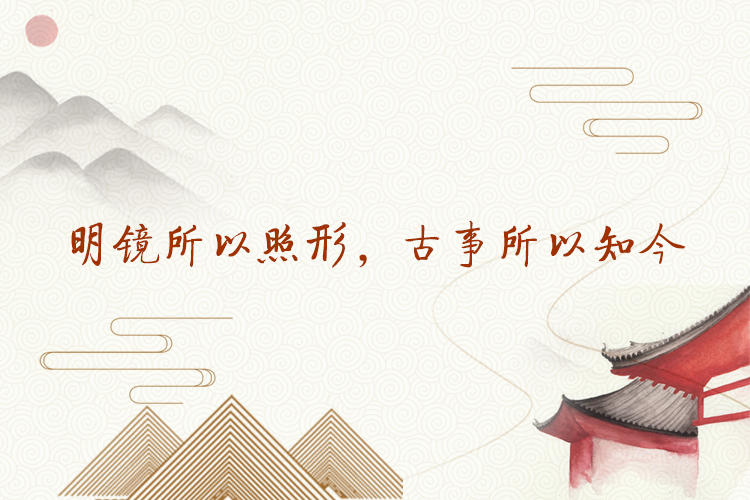
“明鏡所以照形,古事所以知今”這句名言,是2016年7月1日,習(xi) 近平總書(shu) 記在慶祝中國共產(chan) 黨(dang) 成立95周年大會(hui) 上講話時引用的。習(xi) 總書(shu) 記說:‘明鏡所以照形,古事所以知今。’今天,我們(men) 回顧曆史,不是為(wei) 了從(cong) 成功中尋求慰藉,更不是為(wei) 了躺在功勞簿上、為(wei) 回避今天麵臨(lin) 的困難和問題尋找借口,而是為(wei) 了總結曆史經驗、把握曆史規律,增強開拓前進的勇氣和力量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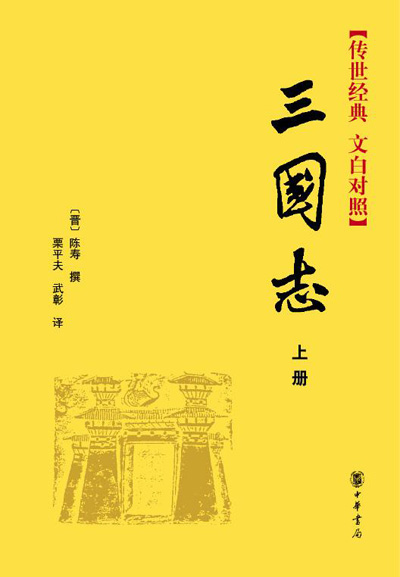
中華書(shu) 局出版的《三國誌》
“明鏡所以照形,古事所以知今”的出處,是陳壽《三國誌》的《吳書(shu) ·孫奮傳(chuan) 》。其具體(ti) 的語境是這樣的:當年孫權有七個(ge) 兒(er) 子,孫奮排行第五,封為(wei) 齊王,居住在武昌。孫權死後,他的幼子孫亮即位。丞相諸葛恪擔心孫亮那些兄長們(men) 權勢太盛,威脅到孫亮的地位,所以就將孫奮遷往豫章,也就是今天的南昌。孫奮本來就是個(ge) 頗有野心的人,如今從(cong) 富庶顯要、兵馬聚集之地被遷往不那麽(me) 重要的豫章,自然心有不滿,不但抗命不遵,而且時有違背禮法的行為(wei) 。此前,孫奮的哥哥孫霸因為(wei) 桀驁不馴,爭(zheng) 奪太子之位,已經被孫權賜死。諸葛恪於(yu) 是就給孫奮寫(xie) 了一封信,結合曆史,特別是孫霸的反麵教訓,給孫奮講了一通身為(wei) 帝胄子孫當以大局為(wei) 重的道理,勸孫奮以往事為(wei) 鑒,所謂“明鏡所以照形,古事所以知今”,如此才能不負身份,不但可以保身,而且有利於(yu) 天下國家。
不過,孫奮並沒有完全聽從(cong) 諸葛恪的勸告,當時雖然遷往豫章之地,但他仍然桀驁不馴,多行不法。其最終的結局,是被後來的吳主孫皓賜死。其實,也不僅(jin) 僅(jin) 是孫奮,孫權的七個(ge) 兒(er) 子,最後的人生結局都不太好,基本上都死在皇室的殘酷內(nei) 鬥之中了。這真是令人感慨。當年曹操看到年輕英俊、神采飛揚的孫權,想到自己的老對手孫堅竟然有這麽(me) 優(you) 秀的兒(er) 子,不由得感歎了一句:“生子當如孫仲謀。”古代漢語的表達比現代漢語有更多的模糊性,要是不看上下文,這句話既可以翻譯成“好想生個(ge) 孫仲謀那樣的兒(er) 子”,也可以翻譯成“好想像孫仲謀那樣生兒(er) 子”。現在看來,“生個(ge) 像孫仲謀那樣的兒(er) 子”是令人羨慕的,但是如果“像孫仲謀那樣生兒(er) 子”可真的就是人間的悲劇了。
這句話的原文出處以及上下文的語境就是這樣。不過,要說到把曆史當作鏡子,這個(ge) 提法的專(zhuan) 利權可不在《三國誌》;而這句話所具有的意義(yi) ,就更不局限於(yu) 孫奮不聽規勸、最後身死的一人一事了。查找史籍,其實不少古人都有過類似的說法。早於(yu) 《三國誌》的,比如漢代賈誼的《新書(shu) 》就說:“明鑒所以照形也,往古所以知今也。”晚於(yu) 《三國誌》的,比如《後漢書(shu) ?馮(feng) 異列傳(chuan) 》也有這樣的話:“明鏡所以照形,往古所以知今。”而讓“鏡子說”聞名天下的,莫過於(yu) 《舊唐書(shu) ·魏徵傳(chuan) 》,根據文中的記載,當魏徵死後,唐太宗說了一段無限感傷(shang) 而又意味深長的話:“夫以銅為(wei) 鏡,可以正衣冠;以古為(wei) 鏡,可以知興(xing) 替;以人為(wei) 鏡,可以明得失。朕常保此三鏡,以防己過。今魏徵殂逝,遂亡一鏡矣!”所有這些,都說明了一點:以史為(wei) 鏡,乃是受到中國社會(hui) 廣泛認可的一種共識。
從(cong) 曆史上來看,使用“以史為(wei) 鑒”這句話的語境,大多是在廟堂之上,又特別集中在和帝王這一級別相關(guan) 的場景中。為(wei) 什麽(me) 會(hui) 這樣?我們(men) 至少可以舉(ju) 出兩(liang) 大理由。
第一,前代的曆史能夠給君王治理國家提供最直接而生動的參考例證。個(ge) 中道理顯而易見,咱們(men) 打個(ge) 比方,這就好比一個(ge) 軍(jun) 事將領要學習(xi) 戰爭(zheng) 的藝術,《孫子兵法》之類講述戰爭(zheng) 基本規律的兵書(shu) 固然重要,但比這更重要的其實還是以往的戰例,因為(wei) 戰例的生動性和豐(feng) 富性要遠遠超過幾句幹巴巴的大原則,將領們(men) 可以從(cong) 中學習(xi) 到更多具體(ti) 可用、行之有效的技法。對於(yu) 君王來說,曆史的作用就好比戰例對於(yu) 軍(jun) 事家。中國的正史,都是以帝王為(wei) 主線寫(xie) 成的,記載了曆代君王治亂(luan) 興(xing) 衰的實例,可以給君王的學習(xi) 提供具體(ti) 的實例;人物傳(chuan) 記中,半數以上是大臣,內(nei) 有忠奸善惡,各色人等,它又可以供君王揣摩鑒別選拔人才的具體(ti) 方法。在這個(ge) 意義(yi) 上,曆史就是最好的帝王教科書(shu) 。我們(men) 知道,北宋曆史學家司馬光有一部曆史名著叫《資治通鑒》,而多數人不知道的是,《資治通鑒》原來並不叫這個(ge) 名字,而是叫做《通誌》,通達的通,誌向的誌,書(shu) 寫(xie) 成以後,引起了宋神宗的高度重視,他認為(wei) 這部書(shu) ,鑒於(yu) 往事,有資於(yu) 治道,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這部書(shu) 以往事為(wei) 鑒,對於(yu) 治理天下大有好處,於(yu) 是賜名《資治通鑒》,神宗的話實在是把曆史書(shu) 對於(yu) 君王的意義(yi) 說到家了。我們(men) 經常聽到有人抱怨,說中國的正史,無異於(yu) 帝王將相的家譜,像關(guan) 漢卿、王實甫這樣閃閃發光的名字是找不到的,一大堆庸庸碌碌的官員甚至是貪官汙吏反倒名列其中。這個(ge) 抱怨說的是實情,但他們(men) 忘記了一個(ge) 基本事實,那就是中國的曆史特別是正史,在其編撰者看來,最重要的或者說第一假想讀者不是學者而是帝王,編撰的第一要義(yi) 並不在於(yu) 銘記那些優(you) 秀人物,而在於(yu) 為(wei) 帝王治理天下提供一麵鏡子。
第二,是給君王一個(ge) 強有力的約束。之所以如此,有中國特別的曆史文化原因。從(cong) 周朝開始,中國人對鬼神的崇拜就遠較商朝為(wei) 弱,神權對於(yu) 政權的約束力,就不像古代的歐洲等地那麽(me) 強烈;到了秦漢以後,君主專(zhuan) 製愈演愈烈,人間就更沒有什麽(me) 權力能夠與(yu) 君主相抗衡了。而按照馬克思的說法,在君主製的國家裏,君主既是整個(ge) 國家製度中最為(wei) 關(guan) 鍵的一環,又是最為(wei) 任性的一環,一旦出了問題,對整個(ge) 國家的影響就是極其嚴(yan) 重的。那麽(me) ,究竟怎樣才能對人間君主的行為(wei) 有所約束、有所引導呢?中國的政治哲學家也找到了一些途徑,比如“天命觀”,比如“天人感應”、諫官製度等,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(ge) 舉(ju) 措,就是史官製度。在中國古代,史官是不離君王左右的,一切言行,均由史官記錄在案,這就是所謂的“起居注”,並且按照規矩,君主本人是沒有查閱自己起居注的權利的;而一旦舊王朝終結,新王朝的一個(ge) 重要任務,就是撰寫(xie) 前朝的曆史,總結前朝的經驗教訓,給前朝的人物特別是君王蓋棺定論。因為(wei) 所有的曆史都是以帝王為(wei) 主線的,這就把所有的君王都納入到了曆史的統緒之中。這也給了君王一個(ge) 強烈的提示:好的君王可以流芳百世,不好的則會(hui) 留下罵名。一般而言,人總不願意給後人,特別是自己的後世子孫留下罵名。而要留下好的名聲,就要約束自己的欲望,注意自己的言行。曆史對於(yu) 在上位者的作用大體(ti) 就是這樣。
那麽(me) ,是不是說它對於(yu) 我們(men) 普通人就沒有什麽(me) 參考意義(yi) 了呢?絕對不是。一方麵,大到國家也好,小到企業(ye) 、單位、甚至是家庭也好,規模不同,但有一些基本的規律還是相同的。通過曆史,可以為(wei) 我們(men) 、特別是肩負各種領導職責的人們(men) ,處理自己工作生活中的各種事務提供可資參考的借鑒。另一方麵,也是對我們(men) 普通人更有意義(yi) 的,是曆史為(wei) 我們(men) 的人生選擇提供了豐(feng) 富的榜樣。人的成長是需要榜樣的,榜樣明晰了,我們(men) 就可以對標學習(xi) ,更好地成為(wei) 我們(men) 想要成為(wei) 的那種人。現實生活當中,我們(men) 的交遊、視野是有限的,有時很難找到令我們(men) 心儀(yi) 的榜樣。這時,曆史就可以助我們(men) 一臂之力。太陽底下無新事,人類所能出現的各色人等,在曆史中基本都能找到。放眼曆史,通過對曆史人物的甄別、反思,就能夠開闊我們(men) 的視野,視野開闊了,人生格局往往也就會(hui) 隨之而改變。
關(guan) 於(yu) 我們(men) 聯係我們(men) 網站地圖 用戶調查
ky体育中心 版權所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