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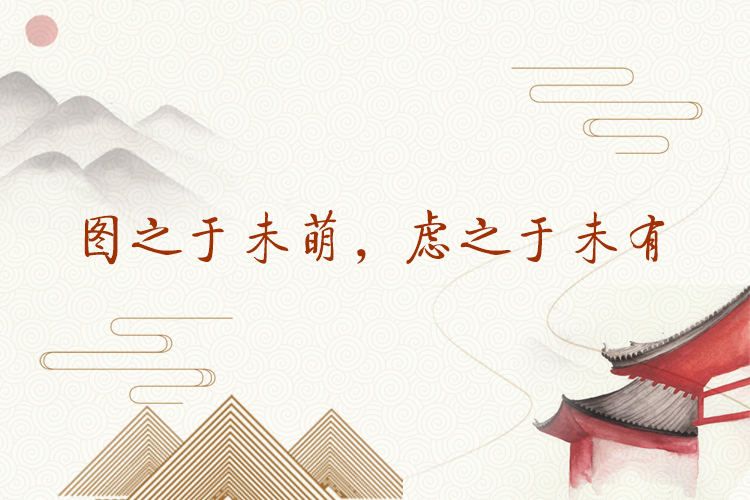
“圖之於(yu) 未萌,慮之於(yu) 未有”,是2015年10月29日習(xi) 近平總書(shu) 記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(hui) 第二次全體(ti) 會(hui) 議上提到下大氣力破解製約如期全麵建成小康社會(hui) 的重點難點問題時引用的。習(xi) 總書(shu) 記說:“今後5年,可能是我國發展麵臨(lin) 的各方麵風險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。我們(men) 麵臨(lin) 的重大風險,既包括國內(nei) 的經濟、政治、意識形態、社會(hui) 風險以及來自自然界的風險,也包括國際經濟、政治、軍(jun) 事風險等。如果發生重大風險又扛不住,國家安全就可能麵臨(lin) 重大威脅,全麵建成小康社會(hui) 進程就可能被迫中斷。我們(men) 必須把防風險擺在突出位置,‘圖之於(yu) 未萌,慮之於(yu) 未有’,力爭(zheng) 不出現重大風險或在出現重大風險時扛得住、過得去。”

中華書(shu) 局出版的《舊唐書(shu) 》
“圖之於(yu) 未萌,慮之於(yu) 未有”的出處,是唐代大臣柳澤給唐睿宗李旦的一封奏疏。此篇奏疏,最早見於(yu) 後晉劉昫等撰寫(xie) 的《舊唐書(shu) ·柳亨傳(chuan) 》所附的《柳澤傳(chuan) 》,後被收錄在《全唐文》中。
柳澤,生卒年不詳,蒲州(今山西運城)人。睿宗時任監察禦史,玄宗時任太子右庶子。後被委任為(wei) 鄭州刺史,未及成行,即患病身死,追贈兵部侍郎。
這封奏疏的寫(xie) 作背景,是唐睿宗李旦第二次被立為(wei) 皇帝後不久。李旦是唐高宗李治與(yu) 武則天的兒(er) 子,他曾兩(liang) 次讓出皇帝之位,在中國曆代皇帝中,其經曆也算得上是一段傳(chuan) 奇。他第一次當皇帝,是他的哥哥唐中宗李顯因為(wei) 不肯當母親(qin) 武則天的傀儡而被廢掉之後。後來武則天稱帝,李旦將皇位讓給了自己的母親(qin) 。這是其第一次讓出皇帝之位。他第二次當皇帝,是中宗李顯駕崩,將皇位傳(chuan) 給自己的兒(er) 子少帝李重茂,李旦的兒(er) 子臨(lin) 淄王李隆基聯合鎮國太平公主發動政變,殺死韋後、安樂(le) 公主,廢掉少帝,擁立李旦為(wei) 帝。而李旦在兩(liang) 年之後,又將帝位傳(chuan) 給李隆基,自己做了太上皇,這是其第二次讓出皇帝之位。
柳澤給睿宗上的這封奏疏,談論的主要問題是關(guan) 於(yu) 皇太子——確切地說就是關(guan) 於(yu) 後來的唐玄宗李隆基的教育培養(yang) 問題。李隆基能夠聯合鎮國太平公主,在錯綜複雜、稍瞬即變的政局中一舉(ju) 拿下韋皇後、安樂(le) 公主,其政治素質是有目共睹的。但他也有很明顯的問題,就是喜歡奢侈享受,喜歡音樂(le) 歌舞,喜歡打獵遊玩,這些都讓柳澤感到十分擔憂。如果沒有太大的變故,李隆基將來當皇帝,應該說是板上釘釘的事情,假如他帶著這些問題登上權力的頂峰,一定會(hui) 給大唐帶來一些麻煩。柳澤給睿宗上這封奏疏,就是希望睿宗能夠注意到李隆基身上的這些缺點,並加以訓導和改正:“誕降謀訓,敦勤學業(ye) ,示之以好惡,陳之以成敗,以義(yi) 製事,以禮製心,圖之於(yu) 未萌,慮之於(yu) 未有,則福祿長享,與(yu) 國並休矣。” ——對太子身上的毛病,要多加留意,時時加以訓導,告訴他什麽(me) 是好的,什麽(me) 是壞的;做什麽(me) 會(hui) 導致成功,做什麽(me) 會(hui) 導致失敗;用道義(yi) 指導做事,用禮法約束心性;在禍患沒有萌發之前就預先準備,在災難沒有到來之時就預先防備。這樣的話,個(ge) 人可以長保富貴,國家也可以永保太平。
柳澤的奏疏,睿宗表示讚賞,還將其提拔為(wei) 監察禦史。不過,讓柳澤始料未及的是,睿宗對當皇帝似乎沒什麽(me) 熱情,很快就把皇位傳(chuan) 給了李隆基,所以柳澤的這些建議,等於(yu) 是沒有起到什麽(me) 作用,李隆基仍然帶著讓柳澤擔心的那些缺點做了大唐的新一代天子,就是唐玄宗。後來的結果我們(men) 也知道了,唐玄宗李隆基才幹非凡,繼位之後任用姚崇、宋璟等一批賢臣,很快將大唐帶入了一個(ge) 全新的局麵,迎來了中國曆史上堪稱輝煌的“開元盛世”;但也正像柳澤所擔心的那樣,唐玄宗喜歡奢侈享受,喜歡音樂(le) 歌舞,喜歡鬥狗走馬,這些給盛世的背後埋下了隱憂,讓大唐在極度繁榮之後不久,就走向了衰落。我們(men) 在惋惜之餘(yu) ,還真是要佩服柳澤的先見之明。
“圖之於(yu) 未萌,慮之於(yu) 未有”的出處和史實就是這樣。不過,我們(men) 要說明的是,這句話雖然是柳澤說的,但核心意旨卻來自於(yu) 中國的文化傳(chuan) 統,類似的表述在中國典籍中所在多有。比如《老子》說:“為(wei) 之於(yu) 未有,治之於(yu) 未亂(luan) 。”《管子·牧民》說:“唯有道者,能備患於(yu) 未形也,故禍不萌。”《禮記·中庸》說:“凡事豫則立,不豫則廢。言前定則不跲,事前定則不困,行前定則不疚,道前定則不窮。”《黃帝內(nei) 經》說:“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,不治已亂(luan) 治未亂(luan) ,此之謂也。夫病已成而後藥之,亂(luan) 已成而後治之,譬猶渴而穿井,鬥而鑄錐,不亦晚乎。”所有這些,都是強調要在不好的跡象剛剛冒出苗頭,災禍還沒有形成的時候就善加預防。
這裏麵有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,也有未雨綢繆方能事半功倍的經驗和智慧。
《韓非子》一書(shu) 中,扁鵲為(wei) 蔡桓公看病的例子就說明了這個(ge) 道理。扁鵲見到了蔡桓公,說您生病了,病灶在皮膚的紋理之間,不治療的話恐怕會(hui) 加重。蔡桓公說我沒病。扁鵲出去後,蔡桓公就對左右說,醫生就是這樣,喜歡給沒病的人治病,然後說成是自己的功勞。過了十幾天,扁鵲再次來見蔡桓公,說您的病在肌肉和皮膚之間了,不治的話就越來越嚴(yan) 重了。蔡桓公沒有搭理扁鵲。又過了十天,扁鵲又來了,說您的病在腸胃之間了,不治的話就越來越重了啊!蔡桓公還是沒有搭理扁鵲。又過了十天,扁鵲見到蔡桓公,一句話沒說,扭頭就走。蔡桓公覺得奇怪,就派人問他。扁鵲說病在皮膚的紋理,熱敷之類的手段就能治好;病在肌膚,針灸之類的手段就能治好;病在腸胃,湯藥之類的手段也還能治好;病在骨髓,那是死神的事,什麽(me) 手段都治不了了。又過了五天,蔡桓公身體(ti) 疼痛,再派人找扁鵲,扁鵲早就跑到秦國去了,於(yu) 是蔡桓公就死了。
韓非子講這個(ge) 故事,目的當然不是在說治病,而是由“良醫之治病也,攻之於(yu) 腠理”的道理,推及到國家治理的道理,所謂“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也”。他接著舉(ju) 了晉公子重耳也就是後來的晉文公流亡時經過鄭國的故事。重耳經過鄭國,鄭國國君對他非常輕視。叔瞻勸諫鄭君,說重耳是賢公子,您應當禮貌地待他。見鄭君不聽,叔瞻又勸諫,說如果您不能厚待他,幹脆就殺了他,以絕後患。鄭君還是不聽。後來的事情我們(men) 也都知道了,重耳流亡十幾年後回到晉國,成為(wei) 晉國的國君,很快就發兵打敗鄭國。春秋時候的戰爭(zheng) 是不以滅國為(wei) 目的的,但即便如此,晉文公還是奪取了鄭國的八座城市,表示對鄭君的懲罰。當晉公子重耳落魄流亡時,一頓好飯,一杯好酒,一次溫暖的談話,就可以與(yu) 他交好,使鄭國在將來可以擁有一個(ge) 強大的後盾;或者趁重耳流離失所,身邊隻有十幾個(ge) 麵黃肌瘦的舊門客追隨左右時,帶著一隊士兵,輕易奪取他們(men) 的性命,這樣鄭國將來就會(hui) 少了一個(ge) 與(yu) 己為(wei) 敵的雄霸之主。鄭君缺乏這種遠見,當然就會(hui) 為(wei) 自己的短視付出代價(jia) 。
古人這種深切的憂患意識,以及未雨綢繆的智慧,具有著穿越時空的永恒價(jia) 值,在今天,依然具有借鑒意義(yi) 。正如習(xi) 總書(shu) 記所指出的,改革已經到了深水區,今後一段時間,很可能是我國發展麵臨(lin) 的各方麵風險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。這些風險,既包括內(nei) 部的,也包括外部的。麵對這些風險,正確的態度,就是所謂“圖之於(yu) 未萌,慮之於(yu) 未有”。當然,“圖之於(yu) 未萌,慮之於(yu) 未有”是一個(ge) 態度,是一個(ge) 戰略,對於(yu) 不同性質的問題,所采取的對策也還是有所不同的。對於(yu) 來自內(nei) 部的、相對可控的問題,“圖之於(yu) 未萌,慮之於(yu) 未有”體(ti) 現在風險剛露出苗頭的時候就盡量消除,不要養(yang) 癰貽患,努力避免重大問題的出現。比來自內(nei) 部風險更為(wei) 複雜的是那些來自外部的風險,因為(wei) 這些風險是否到來以及程度如何不是我們(men) 所能控製的。麵對這種問題,“圖之於(yu) 未萌,慮之於(yu) 未有”則表現在練好內(nei) 功,提早準備,即《孫子兵法》所謂“昔之善戰者,先為(wei) 不可勝,以待敵之可勝。不可勝在己,可勝在敵”,把自己的工作做好,保持一種不可戰勝的狀態,這樣,就能保證在重大風險來臨(lin) 的時候,能夠扛得住、過得去,柳暗花明,化險為(wei) 夷。
關(guan) 於(yu) 我們(men) 聯係我們(men) 網站地圖 用戶調查
ky体育中心 版權所有